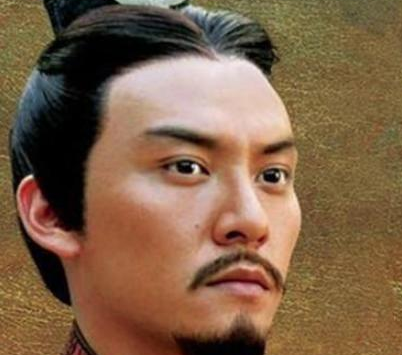关于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之关系,戴伟华曾在《唐代幕府与文学》中指出:“幕府之幕就是帐幕,古代将军出征时,以随地驻屯的营幕为办公之所,这个军事指挥部就叫幕府。幕府有武将,也有文官,故幕府一开,文士们便纷纷涌入。他们有的是为了实现自己救世济民的理想;有的是为了以此为仕进的阶梯; 还有的是为了生计而奔走。尽管目的不同,想法不一,幕府的生活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情况确实如其所言。科举之外,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很多,入幕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不少士子,都有过任职幕府的体验,李白、杜甫、王维、王翰、高适、岑参、元结等都曾在幕府生活过。
中唐以后,入幕更是许多士人的主要仕途经历。幕府的生活不但影响了文士们的前途,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生活态度,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本文仅以盛唐诗人高适为例,浅谈入河西哥舒翰幕府对其诗歌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高适入河西幕府之时间与因由
“河西”之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自此河西正式归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河西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和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高适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旧唐书》《新唐书》本传都有记载。但关于入幕时间,两书均未说明。学者对此说法不一。对于诗人入幕时间的确定,直接关系到对其在幕府期间诗歌创作的统计,是高适河西之行及其诗作研究的基础。那么,高适究竟何时赴西,入哥舒翰幕府的呢? 不妨以诗为证。
高适有《奉寄平原颜太守》诗,诗中平原守指颜真卿。天宝十二载,颜真卿出任平原太守。天宝秋,高适于河西幕府作此诗遥寄颜真卿,表达敬佩与思念之情。诗末四句,说自己从戎河西,客居天涯,已三次目睹鸿雁南飞。言外之意,诗人在河西已经三年了。以此逆推,诗人入河西幕府的时间当在天宝十一载。另,诗人有《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一诗,诗乃赴河西幕府途中所作。诗人当时眺望洪河及其周围,视线由近及远,从低到高,看到乍起的秋风吹动着白蒿,密布的乌云增添了边地苦寒,连绵的积雪使群山愈显高峻。所云种种正是秋冬之时序,而如此风光也惟在西北边塞方能领略。据此可以判定,高适入河西幕府的时间是天宝十一载秋冬之际。

盛唐广设边防重镇,要者有河东、河西、范阳、剑南、平卢、北庭、安西、朔方、陇右及岭南五府经略使。以地域而言,除北庭、安西和河西三镇外,其余边镇与中原地区相连或接近。高适何以舍近求远赴河西入哥舒翰幕府呢?
原因有二:
一则和天宝后期河西的战略地位有关。唐朝于开元年间实力极速加强,出现所谓开元之治的空前盛况。当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北的吐蕃,他们对河陇地区的抢夺成为唐与吐蕃间军事斗争的焦点,唐朝把精兵强将驻扎于河陇一带,来防御、抵抗吐蕃统治者的寇掠。故而河西成为当时文人入幕之所,那里有着更多仕进与报国的机会等待他们。二则与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对文士的倚重有关。开元、天宝中,吐蕃的强大使河陇地区出现一批戍边猛将,他们浴血沙场,因功封赏。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成为杰出代表。高适入幕之因,与哥舒翰对人才的渴求和重用有关。
高适执意入幕河西,除上述客观原因外,还与其家庭环境和个人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高适成长于官宦家庭,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高适的性格不似大多文人那般柔弱谨慎,而是落拓不羁,不拘小节,可以说,高适身上兼具文气和豪气,从文化修养而言,他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而从性格气质来看,他又与儒家传统知识分子不同,骨子里带着一种豪迈英气,这既是时代所赋予的,又是家庭所影响的。只不过前两次出塞均未能实现诗人的理想和抱负,入幕河西成为诗人最后且唯一的机会。

高适入幕河西,也为稻粱而谋。唐代实行科举制,以才学选拔人才,故达官身亡以后,其子孙便失去荫覆,其家庭多至贫寒。高适一族亦逐渐衰败,至诗人时已完全破落了。所以诗人当时迫切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以解决生存问题。公元 749 年,高适入京应试,举有道科,虽仅授从九品上的封丘尉一职,与诗人的鸿鹄之志相去甚远,但为了生计诗人还是接受了这一卑位。只是诗人发现官场的拜迎虚伪,鞭挞百姓与其性格完全相悖,低微的职务亦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到任后不久便愤然解印而去,其生活再次陷入困境。所以,对诗人来说,入幕河西不仅是完成人生夙愿的绝好时机,还是摆脱生活境遇的一条途径。
高适在河西幕府期间,亲眼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唐与吐蕃间的数次战争,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从戎边塞,立功扬名的政治理想。然而作为文人,高适的收获仍在文学创作上。三年时间内,诗人以亲身体验和感受为内容,写下二十五首作品,再一次获得了边塞诗创作的丰收。这一时期既是高适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其边塞诗创作的结束。安史之乱爆发,诗人离开河西,从此再未涉足边塞,亦无边塞诗问世。事实证明,入幕河西不但使高适诗歌的题材愈加广阔,艺术更趋成熟,写下如《九曲词》等脍炙人口的边塞名篇,而且幕府的特殊经历和诗人境遇、情绪之不同使其创作风格与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二、高适诗歌创作风格的转换: 由“悲壮”气韵转向“豪迈”风格
高适诗歌创作的风格,学者惯以“慷慨悲壮”加以概括形容。诚然,作为盛唐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高适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方面,远超同一时代的诸多诗人,应际而生的建立不朽功业的昂扬意志,和直面惨淡现实的悲慨相融合,令高适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慷慨而悲壮的美。但这有些窥一斑而未见全豹之嫌,未免有点以偏概全。
仔细考察高适入幕河西后创作的诗歌,就会明显地体会出这些诗作大多散发出一股昂扬明朗的气息,洋溢着一种欢快轻松的情调,由原来的“悲壮”气韵转向“豪迈”风格。其中一些写景诗更表现出一种“冲淡”之气,同以往边塞诗所呈现出的悲壮苍凉,苦闷沉重产生一种明显对比。诗歌创作风格的转换,寻其根源,在于诗人前后出塞之情绪、境遇不同。高适一生曾三次出塞,前两次是东北,最后一次是河西,我们称之为前后期。
高适初次以布衣身份出塞,再次以县尉职务出塞,基本上有着相同境遇,即身份卑微,地位低下。故抒写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的悲苦,成为前两次边塞诗歌所表现的主题与目的。入河西幕府,高适的处境和心绪则大有不同。诗人年过半百,达成了从军边塞的夙愿,深得幕主哥舒翰的赏识,其心情自然是爽朗欢乐的。诗人以其笔抒其情,故创作出的作品高昂豪迈,有别于昔。
高适后期诗风之变,突出表现在反映唐蕃战争的诗作中。高适入河西幕府时期,恰为唐蕃之 、间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诗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流畅优美的语言,记录了其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唐蕃间的战和关系。较为突出的,是反映唐蕃争夺黄河九曲之地的一系列佳作。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不像以往反映边塞战争的诗那样暗淡伤感,悲壮苍凉,而表现得比较欢快明朗,高昂豪迈。浅层而言,诗是对幕主哥舒翰的赞赏和对战后百姓生活的描绘。
实际上,通过对骁勇猛将与太平盛世的热烈歌颂,反映诗人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高适对于吐蕃统治者的狼子野心,看得十分透彻明白,认为其欲壑难填,永无止境。所以他反对一味妥协退让,反对和亲,在《塞上》诗中直言“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 和亲非远图。”主张坚决抵抗,指出和亲仅是一种迂回矛盾的手段,而不是争取太平的明智之举。

三、高适诗歌创作审美情趣的转换: 从“映像社会”转向“书写自然”
众所周知,高适的诗多反映社会,很少书写自然,也就是说高适的审美情趣在社会生活而不在自然山水。作为诗人,高适并非不钟爱大自然,也不是不能领略和书写自然山水之美。而是一切的景语都是情语的外在表现。以诗为例,纯粹写景之作是难以见到的,诗内美景,往往融合着诗人的情志,表现着诗人的思想,即所谓情与景在诗歌中互相交融,浑然一体。
如前所述,入幕河西前,高适官途不顺,生活窘迫,虽两次北上出塞,但负担沉重,情绪低落,根本没有心思欣赏塞外风光,书写吟咏。故很少创作描写边塞风光的写景诗。入幕河西后,诗人的仕途生涯发生了重要转变,得到幕主哥舒翰的赏识,并委以掌书记的重任。加之,唐朝在与吐蕃的斗争中屡屡告捷,洗雪前耻,诗人的情绪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起来。闲暇之际,诗人或独自,或约友,前往周边登山游湖,聚会欢乐,写下了颇多书写边塞自然风光的写景记游佳品。其诗歌创作的审美情趣开始从“映像社会”转向“书写自然”。
如《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得雷字》诗序,凉州,唐属陇右道,治所在姑臧县即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客观地说,这里既有着边塞共有的偏远苦寒之象,又有着黄河之水孕育出的独特自然风光。可惜在那“车辚辚,马萧萧”的古代绝大多数诗人没有来过凉州,他们往往根据想象和传闻,误认为凉州是一片春风不度,荒凉寂寞的黄沙野地。只有那些身临其境的诗人,方能真实地描绘凉州,也只有他们最具有历史的发言权。高适便是其中为数不多的诗人之一。苏轼评价王维诗说诗中有画,高适的写景诗同样如诗如画,意境清幽,美不胜收。这怎能让人相信诗人当时是在边地要塞凉州,其与同代诗人柳中庸《凉州曲》所说“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之凉州实有天上人间之别!

入幕河西后,高适写景诗的艺术技巧也发生了变化,愈加成熟与高妙。如《入昌松东界山行》一诗“石激水流处,天寒松色间。”以流水之动,反衬山林的清幽寂静。其表现手法和艺术效果与《过香积寺》颈联“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颇为相似。清赵殿成曾对王维这两句诗作过评论,认为其“咽”和“冷”两字用得相当好,前者绘出幽静之状,后者画出深僻之景,是全诗的诗眼。他给予此诗很高评价,但未论及高适之诗。清陈铁民在《高适岑参诗选评》一书中则对王维和高适之诗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从诗眼的提炼上而言,高适诗的确不如王维诗,但就经过打磨锤炼后又回归自然平淡上,高适诗比起王维诗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一针见血,十分客观。这一时期,高适叙述事件、记载出行及抒发情感大都会有景色描绘。
《武威作二首》其一写诗人登高远眺之所见,高峰入云,晴空万里,辽阔无边。《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桥迴登积石军多福七级浮图》:“塞口连浊河,辕门对山寺。”“七级凌太清,千崖列苍翠。”等句以白描手法,写登高远眺,见七级宝塔深入云霄,周围群山草木茂盛。《和窦侍御登凉州七级浮图之作》一诗写从佛塔窗中看到天高地阔,听闻战鼓声声。放眼望去,地处西陲,万里天寒。这些诗写景真实,情感充沛,若非亲眼所见和亲身所感是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的。它们恰好证明了叶燮《原诗》所谓高适诗“时见沉雄,时见冲淡,不一色。”观点之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