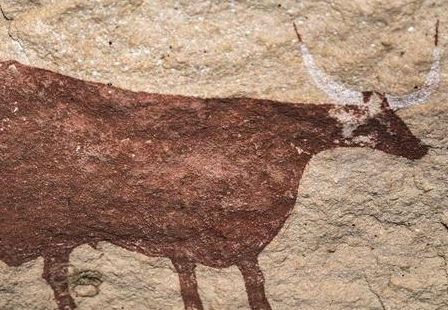1.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学命运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钟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2.魏晋文人包括哪些
曹操 孔融 建安七子 陈琳 刘勰 七子之冠冕”的王粲 阮籍 嵇康 兰亭诗派: 王羲之与谢安、孙绰、支遁等四十一人 蔡邕.陶渊明 才女蔡文姬 文学自觉的思潮在文学发展史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它总是要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它的过渡时期总是充满着迷惘和徘徊。
太康诗风[11]上承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在文学自觉的思潮中徘徊着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作为当时文学主体的创作者认识到,创作个性的自觉总是与现世的政治与社会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文学是理想化的东西,而现实是残酷的,文学是否顺应统治者的现实利益直接关系到当时文人命运的变化。太康时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战乱和分裂,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八王之乱”),使社会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这时的文人处于战乱中为了寻找自保而投身于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为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又极力地拉拢一大批文人,依靠文人的扶持壮大势力。
文人在政治与文学沉浮和互动中,在艺术趣味的追求与政治的冲突中,生与死的徘徊,仕与隐的选择,自觉意识的创作与集团利益的争夺,将他们置于两难的境地。作家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朝代的更替,他们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最终成为了政治集团利益的牺牲品。
太康文人在当时有很强的功名心。在许多文人看来,文学成为他们寻求自保、博取功名的手段,逞才是创作的目标。
为求功名,陆氏兄弟背井离乡,千里入洛,“静幽谷底,长啸高山岑”,功名未就又“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般的感叹(陆机《猛虎行》);左思之志“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咏史诗八首》其一)。而当时魏晋时代又是一个门阀制度的时代,许多寒士怀抱志向,身负才学,迫切希望改变他们的政治处境,又不得不依附于统治集团。
太康作家群,一开始就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文人群体,潘,陆,左,刘等诗坛名流与不能入流的大小诗人,寒素之士与名门望族,权臣与游士,他们在政治与名利的洪流中莫名其妙地卷入,又进行了毫无道义的残酷杀夺,最终连自己也遭受到杀戮,值得一提的是太康文人是死于王侯之间的阴谋与夺杀,而他们自己又是“阴谋与杀夺”的组成部分。冷酷的现实击碎了太康诗人的功名之梦,利禄功名或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心理处于焦虑和无计消释的境地,敏感的作家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在他们终其一生,临渊覆薄的人生歧路口,在经历了腥风雪雨的杀戮之后,诗人凝定为沉重的生死焦虑,他们绝望地期待消释和拯救[12],他们忍受着心灵的折磨和煎熬,为了寻求解脱和消释,诗文创作又成为他们心灵的慰籍和归宿,在人生漂泊,命运叵测的生命尽头他们不得不反思自我。
陆机临刑时,“欲闻华亭鹤唳”(《世说新语·尤悔》);潘岳经历了夭子,亡妻,逝弟,丧妹的苦痛后,“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谁谓帝宫远,路极悲有余。”(《悼之诗三首》其三),太康文人最后的反思留下的沉重的一笔真实记录了文学自觉在徘徊中的心路历程,他们的反思是必然的,却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学自觉思潮的前进和发展。
时代发展到后来的陶渊明,纯文学创作和文学的“自觉”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极致(在当时来说)。当时偏安一隅的政治格局,柳细花柔的江南山水,旷淡清远的玄学之风,已大大消解了太康文人所具有的种种冲突与焦虑,陶渊明在那个时代最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
他不属于任何集团,却又在文学史上取得了最崇高的地位。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13]。
陶渊明可以说是文人对自身命运反思后要达到圆通和消逝而寻求的一种身后之路。于是,他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
陶渊明作为田园诗题材的开创者,他的文学思想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对中国诗歌思想,影响非常大,陶渊明的创作是远离宫廷的,也远离了政治,文学的“自觉”在他身上是集大成者。冲淡,自然的境界和审美情趣将政治和文学严格的划分开来。
“质性自然”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抱朴”方能“含真”,在自然的状态下可以保持人的天性,从而得到身心的自由。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最园田居》其一)般的“桃花源”境界正是他农耕社会人生理想的结晶。
“桃花源”作为中国文人眼中的乌托邦,它的价值或许还在于其理想的纯粹性,而不在其是否可操作。陶渊明用优美的文学语言,在“桃花源”中展示了一片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圣洁的天地。
“桃花源”诞生于乱世,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是十分明显的,但作者是否意识到,在那样腐败而黑暗的岁月,无论是理想的社会还是精神的家园,都是永难实现的梦幻[14]。“桃花源”作为一个虚无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社会相比较,又永远有着现实的价值。
它在批判现实,呼唤人们改造现实的同时,又可以慰籍人们的心灵,让人超越或逃避于现实。联系陶渊明之前的魏晋文人,他们多半只是在诗歌中归隐,而陶渊明则是实实在在的归隐[15],魏晋文学和人格最高境界,在陶渊明的。
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文学命运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
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
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
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
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
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
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
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
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
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
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
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闲居赋》。
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钟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
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4.魏晋文人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
文学自觉的思潮在文学发展史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它总是要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它的过渡时期总是充满着迷惘和徘徊。
太康诗风[11]上承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在文学自觉的思潮中徘徊着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作为当时文学主体的创作者认识到,创作个性的自觉总是与现世的政治与社会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文学是理想化的东西,而现实是残酷的,文学是否顺应统治者的现实利益直接关系到当时文人命运的变化。太康时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战乱和分裂,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八王之乱”),使社会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这时的文人处于战乱中为了寻找自保而投身于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为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又极力地拉拢一大批文人,依靠文人的扶持壮大势力。
文人在政治与文学沉浮和互动中,在艺术趣味的追求与政治的冲突中,生与死的徘徊,仕与隐的选择,自觉意识的创作与集团利益的争夺,将他们置于两难的境地。作家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朝代的更替,他们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最终成为了政治集团利益的牺牲品。
太康文人在当时有很强的功名心。在许多文人看来,文学成为他们寻求自保、博取功名的手段,逞才是创作的目标。
为求功名,陆氏兄弟背井离乡,千里入洛,“静幽谷底,长啸高山岑”,功名未就又“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般的感叹(陆机《猛虎行》);左思之志“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咏史诗八首》其一)。而当时魏晋时代又是一个门阀制度的时代,许多寒士怀抱志向,身负才学,迫切希望改变他们的政治处境,又不得不依附于统治集团。
太康作家群,一开始就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文人群体,潘,陆,左,刘等诗坛名流与不能入流的大小诗人,寒素之士与名门望族,权臣与游士,他们在政治与名利的洪流中莫名其妙地卷入,又进行了毫无道义的残酷杀夺,最终连自己也遭受到杀戮,值得一提的是太康文人是死于王侯之间的阴谋与夺杀,而他们自己又是“阴谋与杀夺”的组成部分。冷酷的现实击碎了太康诗人的功名之梦,利禄功名或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心理处于焦虑和无计消释的境地,敏感的作家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在他们终其一生,临渊覆薄的人生歧路口,在经历了腥风雪雨的杀戮之后,诗人凝定为沉重的生死焦虑,他们绝望地期待消释和拯救[12],他们忍受着心灵的折磨和煎熬,为了寻求解脱和消释,诗文创作又成为他们心灵的慰籍和归宿,在人生漂泊,命运叵测的生命尽头他们不得不反思自我。
陆机临刑时,“欲闻华亭鹤唳”(《世说新语·尤悔》);潘岳经历了夭子,亡妻,逝弟,丧妹的苦痛后,“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谁谓帝宫远,路极悲有余。”(《悼之诗三首》其三),太康文人最后的反思留下的沉重的一笔真实记录了文学自觉在徘徊中的心路历程,他们的反思是必然的,却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学自觉思潮的前进和发展。
时代发展到后来的陶渊明,纯文学创作和文学的“自觉”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极致(在当时来说)。当时偏安一隅的政治格局,柳细花柔的江南山水,旷淡清远的玄学之风,已大大消解了太康文人所具有的种种冲突与焦虑,陶渊明在那个时代最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
他不属于任何集团,却又在文学史上取得了最崇高的地位。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13]。
陶渊明可以说是文人对自身命运反思后要达到圆通和消逝而寻求的一种身后之路。于是,他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
陶渊明作为田园诗题材的开创者,他的文学思想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对中国诗歌思想,影响非常大,陶渊明的创作是远离宫廷的,也远离了政治,文学的“自觉”在他身上是集大成者。冲淡,自然的境界和审美情趣将政治和文学严格的划分开来。
“质性自然”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抱朴”方能“含真”,在自然的状态下可以保持人的天性,从而得到身心的自由。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最园田居》其一)般的“桃花源”境界正是他农耕社会人生理想的结晶。
“桃花源”作为中国文人眼中的乌托邦,它的价值或许还在于其理想的纯粹性,而不在其是否可操作。陶渊明用优美的文学语言,在“桃花源”中展示了一片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圣洁的天地。
“桃花源”诞生于乱世,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是十分明显的,但作者是否意识到,在那样腐败而黑暗的岁月,无论是理想的社会还是精神的家园,都是永难实现的梦幻[14]。“桃花源”作为一个虚无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社会相比较,又永远有着现实的价值。
它在批判现实,呼唤人们改造现实的同时,又可以慰籍人们的心灵,让人超越或逃避于现实。联系陶渊明之前的魏晋文人,他们多半只是在诗歌中归隐,而陶渊明则是实实在在的归隐[15],魏晋文学和人格最高境界,在陶渊明的归隐和创作中达到了诗性情致的终极。
总的看来,文学“自觉”的思潮贯穿魏晋的始终,它在各个文学派中表现的程度各有差别。魏晋文。
5.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有哪些喜好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穿着方面,穿宽大的衣服,穿木屐,这个习惯未必与服用五石散有关。先秦时期时期儒生就爱穿宽大的衣服,汉朝时穿木屐就是一种风尚了。
公元三四世纪,随着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饮茶的风俗沿长江中下游流传开来。魏晋南北朝时,在江南,包括东南沿海,饮茶之风在世族士族中日盛,成为社会活动的一种媒介。在这种风气感染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的豪门士族也有不少喜好饮茶。
还有个不太常说的,其实魏晋南北朝男风盛行。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既是社会上男子讲究仪容装饰的审美因素的结果,也是当时战乱四起、礼教松弛、社会在婚爱方面的引导和教化逐渐减弱的社会因素的结果。它既引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同xing恋文学的繁荣,也颠覆了男女婚配生活这种传统婚姻形式,对传统礼教产生了破坏。
魏晋南北朝还是赌博盛行的时代。赌博者遍布社会各阶层,上自皇帝、官僚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纷纷沉迷其中。这一时期的赌博,与前代或后世相比,更加普遍化、公开化、社会化,呈畸形繁荣之态。当时凡带有竞技色彩、能决出胜负的游戏都可作为决赌之具,但更为经常和主要的赌博活动,则是樗蒲、围棋、弹棋、握搠(双陆)、斗鸡等戏。
魏晋南北朝文人之间经常进行辩论。这种辩论之风是受这个时代自由的学术空气所影响的。不仅清谈玄学独擅辩论,而且儒、佛、道也敢互争高低,各不相让。对这些现象统 治者不仅默许,而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梁简文帝"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分中庶子徐擒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擒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戚)兖说朝聘义,擒与往复,衮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
6.魏晋文人、魏晋风度有关的论文,3000字左右
摘要: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酒在魏晋文人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王羲之与朋友们徜徉于会稽的名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陶渊明在“桃花源”中饮酒种菊,怡然自乐……为什么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间如此盛行呢?魏晋文人与酒有什么联系?它们之间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阐释魏晋文人与酒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魏晋文人 酒 精神寄托 希腊神话中的谬斯,兼职诗神,他的本职工作则是酒神,由此可见,那个文化深远的民族认为,酒之于诗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酒,所以诗。而中国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同样是密不可分的。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酒在魏晋文人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王羲之与朋友们徜徉于会稽的名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陶渊明在“桃花源”中饮酒种菊,怡然自乐…… 为什么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间如此盛行呢? 有一种说法,是与服药有关。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曹操的女婿、魏晋名士何晏首倡服药,他那时既有权又有钱,开始服用一种叫“五石散”的补药,“人吃了能转弱为强”,有着使人神清气爽、延年益寿的效果。
服“五石散”不但极贵而且极麻烦,特别要紧的是服药之后必须饮热酒,不然便会有性命之忧。由于何晏带头,当时的才子王弼和大将军曹爽的外甥夏侯玄参与推波助澜,在统治阶级的社会名流中便服药成风,与之同时,纵酒也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寒门文人极普通老百姓虽然服不起药,却也喜欢打着这个旗号饮酒,乐得自由。
然而,各位文人饮酒的原因却也不尽相同。 曹孟德曾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曹操喝酒,是为了解忧。他忧的是什么?曹操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中国,他所忧愁的便是得不到众多的贤士人才来同他一道建功立业。
因此,曹操喝酒,表面看似“以酒浇愁”的消极行为,实则表达了他阔达的政治家胸襟,求贤若渴的心情,建功立业的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精神。 “竹林七贤”都喜饮酒,尤其以阮籍和刘伶最甚。
当时正是司马氏正积极准备篡位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司马氏注意的人物,但他们都不买司马氏的账;他们在一起饮酒自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们的对策是不拘形迹地饮酒,平时言谈举止也异于常人。
比如刘伶喜在家中赤身裸体饮酒,有人说他的不是,他反而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房屋当做衣裤,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面来了?阮籍则是以醉酒来搪塞司马氏的拉拢,他的名气很大,司马昭打算和他结儿女亲家。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使得司马昭没有提亲的机会,只好作罢算了。
由此可见,他们饮酒是以买醉逃避不满的现实,是对魏晋政权交替中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这实实在在的纵酒却也正合乎人民当时在动荡生活得需要,并为破除礼教中一些限制饮酒的规律找到了依据。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淡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
王羲之与友人们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之外”,“引以为流觞曲水”,“一觞一咏”,尽情享受着饮酒创作的乐趣。王羲之能够创造出享有盛名的书法奇作《兰亭集序》,酒无疑成了助其形神相亲的妙剂。
王羲之饮酒,是因为酒是其艺术创作的助推剂。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酒已成为他的象征。
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
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陶渊明饮酒,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中如此盛行,尽管原因不尽相同,酒都扮演了精神寄托的角色。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
战乱和分裂是这个时期的特征。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敏感的文人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因此,酒及时地成为了魏晋文人所寄托的精神食粮。
酒可以让他们暂时地摆脱形体桎梏,忘记乱世的烦恼,让精神得到一丝解脱,聊以慰藉遍体鳞伤的心灵。 曹操“对酒当歌”,寄以求贤之渴,由此召集天下贤士,建功立业,终结束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统一了中原;“竹林七贤”买醉以逃现实之祸,纵使虚无、随便,放荡不羁,故作旷达,也。
7.请问魏晋有哪些文人 能介绍稍微详细一点吗
三曹:指汉魏间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政治地位和文学成就对当时很有影响,后人合称之为
三曹七子
“三曹”:曹操曹植曹丕
七子: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得到后世普遍承认。
竹林七贤
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
8.魏晋文人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
文学自觉的思潮在文学发展史中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它总是要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它的过渡时期总是充满着迷惘和徘徊。
太康诗风[11]上承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在文学自觉的思潮中徘徊着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作为当时文学主体的创作者认识到,创作个性的自觉总是与现世的政治与社会存在着激烈的冲突。
文学是理想化的东西,而现实是残酷的,文学是否顺应统治者的现实利益直接关系到当时文人命运的变化。太康时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战乱和分裂,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八王之乱”),使社会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这时的文人处于战乱中为了寻找自保而投身于统治集团;而统治集团为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又极力地拉拢一大批文人,依靠文人的扶持壮大势力。
文人在政治与文学沉浮和互动中,在艺术趣味的追求与政治的冲突中,生与死的徘徊,仕与隐的选择,自觉意识的创作与集团利益的争夺,将他们置于两难的境地。作家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朝代的更替,他们在政治与文学的夹缝中最终成为了政治集团利益的牺牲品。
太康文人在当时有很强的功名心。在许多文人看来,文学成为他们寻求自保、博取功名的手段,逞才是创作的目标。
为求功名,陆氏兄弟背井离乡,千里入洛,“静幽谷底,长啸高山岑”,功名未就又“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般的感叹(陆机《猛虎行》);左思之志“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咏史诗八首》其一)。而当时魏晋时代又是一个门阀制度的时代,许多寒士怀抱志向,身负才学,迫切希望改变他们的政治处境,又不得不依附于统治集团。
太康作家群,一开始就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文人群体,潘,陆,左,刘等诗坛名流与不能入流的大小诗人,寒素之士与名门望族,权臣与游士,他们在政治与名利的洪流中莫名其妙地卷入,又进行了毫无道义的残酷杀夺,最终连自己也遭受到杀戮,值得一提的是太康文人是死于王侯之间的阴谋与夺杀,而他们自己又是“阴谋与杀夺”的组成部分。冷酷的现实击碎了太康诗人的功名之梦,利禄功名或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心理处于焦虑和无计消释的境地,敏感的作家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在他们终其一生,临渊覆薄的人生歧路口,在经历了腥风雪雨的杀戮之后,诗人凝定为沉重的生死焦虑,他们绝望地期待消释和拯救[12],他们忍受着心灵的折磨和煎熬,为了寻求解脱和消释,诗文创作又成为他们心灵的慰籍和归宿,在人生漂泊,命运叵测的生命尽头他们不得不反思自我。
陆机临刑时,“欲闻华亭鹤唳”(《世说新语·尤悔》);潘岳经历了夭子,亡妻,逝弟,丧妹的苦痛后,“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谁谓帝宫远,路极悲有余。”(《悼之诗三首》其三),太康文人最后的反思留下的沉重的一笔真实记录了文学自觉在徘徊中的心路历程,他们的反思是必然的,却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学自觉思潮的前进和发展。
时代发展到后来的陶渊明,纯文学创作和文学的“自觉”可以说是发展到了极致(在当时来说)。当时偏安一隅的政治格局,柳细花柔的江南山水,旷淡清远的玄学之风,已大大消解了太康文人所具有的种种冲突与焦虑,陶渊明在那个时代最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
他不属于任何集团,却又在文学史上取得了最崇高的地位。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13]。
陶渊明可以说是文人对自身命运反思后要达到圆通和消逝而寻求的一种身后之路。于是,他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
陶渊明作为田园诗题材的开创者,他的文学思想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对中国诗歌思想,影响非常大,陶渊明的创作是远离宫廷的,也远离了政治,文学的“自觉”在他身上是集大成者。冲淡,自然的境界和审美情趣将政治和文学严格的划分开来。
“质性自然”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抱朴”方能“含真”,在自然的状态下可以保持人的天性,从而得到身心的自由。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最园田居》其一)般的“桃花源”境界正是他农耕社会人生理想的结晶。
“桃花源”作为中国文人眼中的乌托邦,它的价值或许还在于其理想的纯粹性,而不在其是否可操作。陶渊明用优美的文学语言,在“桃花源”中展示了一片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圣洁的天地。
“桃花源”诞生于乱世,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是十分明显的,但作者是否意识到,在那样腐败而黑暗的岁月,无论是理想的社会还是精神的家园,都是永难实现的梦幻[14]。“桃花源”作为一个虚无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社会相比较,又永远有着现实的价值。
它在批判现实,呼唤人们改造现实的同时,又可以慰籍人们的心灵,让人超越或逃避于现实。联系陶渊明之前的魏晋文人,他们多半只是在诗歌中归隐,而陶渊明则是实实在在的归隐[15],魏晋文学和人格最高境界,在陶渊明的归隐和创作中达到了诗性情致的终极。
总的看来,文学“自觉”的思潮贯穿魏晋的始终,它在各个文学派中表现的程度各有差别。魏晋文。
9.从魏晋风度中能看出什么人生道理
第二、魏晋风度与文学密切相关。
鲁迅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魏晋风度披靡,文人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文学集团的活跃,注重追求美的创造,文学与哲理的结合。
于是,魏晋文学的异彩表现在创作主体的独特个性上,即“魏晋风度”,它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从而影响文学创作,形成那个时期一些文学的独特的风貌。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