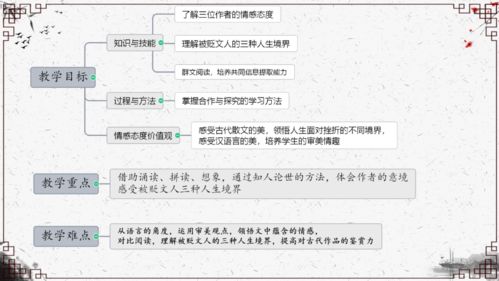
1.被贬谪的历代文人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
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
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技。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檀”去“木”,念“蛋”)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但经断章取义后,句句上纲上线。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
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这位李定正是当年因隐瞒父丧而被司马光称为“禽兽不如”的家伙,苏轼也讥他“不孝”。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轼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皇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
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
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演示自己的才学,抵死不愿作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家人听了故事,心里稍安。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只。
2.中国古代文人被贬谪的成就与其遭遇有何联系
中国古代文人因为被贬,反而在文艺上焕发出新的光芒。
此所谓不平则明。被贬谪后多是受释道思想影响,后人对被贬谪文人多怀敬佩,强调其正面的思想和成就。
被贬之前,那些文人往往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末大憧憬,自己的作品思想和风格中往往包含着此许的世俗之气,还有一些官府之风,再加上一些对朝廷的赞扬。被贬之后,那些文人往往有一些不平之心,也看透了世俗,自己的作品思想和风格早期常有以自己怀才不遇的伤感和愤慨,中期会有些脱俗之气,常常表达出自己对世俗的不屑;而后期时,则真正升华到为民为世,作品思想和风格常以君子之风多些,为民之气多些,反应当时世态多些。
而多数文人,常因被贬之后所作的诗词被后人所知晓. 古代文人贬谪与成就现象具体例举 屈原,“楚辞”的开创者,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出身于贵族之家,与楚王同姓,有着优厚的文化教养,也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献身精神。他希望辅佑楚王,使祖国富强,主张内修法度,联齐抗秦,与朝中的亲秦派形成对立,因楚王昏庸无能、听信谗言,逐渐地被最高统治集团疏远,终于遭致了流放的命运。
在流放江南的岁月里,他忧愤交集地写下了长篇自叙抒情诗《离骚》。 李白,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
其诗歌创作充满了激情与想象,既气势浩瀚,变幻莫测,又自然天成。李白青年时期曾上书安州裴长史、韩朝宗,希求荐用。
天宝元年奉召入京为供奉翰林,但不久就遭到朝中权贵谗毁,于天宝三载以“赐金放还”知名被迫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心怀报国之心的李白加入永王李璘的幕府,又在肃宗李亨讨伐时获“反叛”之罪入狱,长期流放夜郎。
后又想从军报国,终因多病而不能实现。 白居易,中唐时期的杰出诗人,“元和诗风”的代表流派“元白诗派”代表人物,公元802年冬,他在长安应吏部试后于次年步于仕途,曾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太子左赞善大夫之职。
公元815年被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五年,应召回京任职。之后又主动请求外任,历任多个地方州府主事。
晚年则闲居香山,直至去逝。 韩愈,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八大家之首,其“以文为诗”的特点也在诗坛别具一格。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四次科举考试后才得以登第。贞元十九年(公元803),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因上疏要求为关中农民减免赋税,被贬到连州阳山做县令。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应召入京为国子监博士,后升迁为刑部侍郎,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元和十四年(公元879年),因上表力阻宪宗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
后又被召入京任职,官终于吏部侍郎任上而病逝。 刘禹锡 ,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
他的诗歌创作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诗采丰美而笔致流利,被白居易称作“诗豪”。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永州八记》等文章至今是学生必读之作。
贞元九年,他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永贞元年,二人同时参与了王叔文等人的“永贞革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可不久改革失败,二人又同贬为远州刺史。
十年后,二人忽又被诏返京,但不久又被发落到更远的州县任职。从此,柳宗元再没有回京任职,刘禹锡则在调任了多次地方州官后才被调回京度过晚年。
苏轼,是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历经磨练而笑对人生,思想自由,品格坚贞、坦荡、旷达。无论从他的散文、诗、词的哪个方面衡量,他都是宋文学发展到颠峰时期的伟大代表作家,他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和过人的才识。
嘉佑二年,考中进士;嘉佑六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初年,他在朝任职,因从政思想与王安石变法主张多有不同,请求外调。
在外期间由于改不了心直口快、敢于坦诚相言的习性,引发了“乌台诗案”,坐了四个月的监狱,放出之后连削两个官职,贬谪黄州。这就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处于新旧两党的夹击和陷害之中,过着漂泊不定的贫困生活,直至病逝。辛弃疾,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一生以英雄自许,创立了风格独特的“稼轩体”。
他那火一般的爱国热情,贯穿在他的所有的文学作品中。他自幼就有为民族复仇、收复失地的宏大志向。
在朝任职期间,朝廷未让他去抗金,反而让他去镇压农民起义。辛弃疾对此很不满意。
42岁的辛弃疾被免职,开始过了十年的闲居生活,后又被起用,可惜已年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身体有病,获准回家休养,此时北伐已失败,辛弃疾含愤去世。陆游,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其诗歌创作是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在他的近万首诗中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致死不减,这是其诗歌创作的最显著特色。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在战乱中尝尽了颠沛流离的痛苦,这使他从小就萌发了忧国忧民的思想。
在朝任职期间,他一再上书朝廷,反对议和,坚决要求北伐,得罪了朝中主和派,因此被迫罢官,返归山阴。四年后又被起用,但没被重用。
从此过着类似隐居的田园生活约二十年,当他七十八岁时突然又被朝廷下诏起用,他毅然北伐,可惜北伐却失败了,他也因此遭到了不少污蔑打击。八十五岁的陆游含悲去世。
3.以《我看贬谪文人》为题的作文
《我看贬谪文人》
纵观中国的历史长河,我看到了很多文人的生平,他们中有苏轼,有王安石,白居易,有秦观,有欧阳修,有辛弃疾,有陆游,有杜甫,有韩愈,有柳宗元……以前这些人都知道,但整体串起来我却发现了一个现象,这种现象震撼了我,他们很多都是才华横溢,名贯天下,但是,这个群体中有太多的人遭到了当政者的放逐和贬谪,于是,他们靠着流徙完成了在中国一些荒蛮土地上艰辛的文明播种。
我不想重复余秋雨先生《贬官文化》中的内容,中国文人的一些品格实际上是适合当官的,却不适合官场的,文人太直,只知道君王有错只要犯颜直谏便是忠贞;文人太正,一些东西太按规则而不会给任何人留有转空子的机会;文人太清高了,只知道不能和世俗同流;文人太死了,他不知道趋炎附势,只知道国家正统。
所有这些都是文人不适应官场的原因,当政者为了稳固政权给了他们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正统思想,到最后却不习惯由这种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文人,于是,就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贬谪。
中国文人啊,即使遭到贬谪,即使要忍受潮州的湿气,海南的风雨,柳州的瘴疠,北方边境的贫瘠也不后悔。儒家文化教化了他们,他们知道真正的达者要兼济天下,所以明知道会让自己活的很累,但依旧去努力。
在这个中间,李白受挫了,他用“天生我才必有用”来舔拭伤口,孟浩然受挫了,他会用“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来掩饰苦闷,到最后 韩愈去了潮州,杜甫奔波忙碌最后却因为饥饿交加暴饮暴食撑死在江边的一个破船上,而苏轼到最后在海南等了多年的圣旨知道过了花甲才被皇帝想起,最后车马劳顿却终是在回程中客死常州……
但是他们依旧孜孜不倦的去追求,从不后悔。于是出现了今天面前这堵墙上生平相似的人们。
学了一生的孔孟之道,想了一生的兼济天下,换来的却是履历生平中不仅的流徙和凄苦。中国的文人啊,是傻还是聪明?
此情此景,我感悟良多。只愿现在国人都以史为镜,在当今社会的潮流中不断进取,不断进步,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添一砖,加一瓦。
4.古人如何看待贬谪400字
贬官文化,中国历史上因遭贬谪的官员,常常有饱读诗书之人。
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
甚至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些文化便形成了贬官文化。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
诸多的迁客骚人,也成就了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学。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写到:中国历史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
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
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错。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曾间断的现象,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加深了对人性、对制度的思考。
[1] 贬官文人 屈原的《离骚》,千古定评的上乘之作。不过,屈原之后,贬官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演义了一番,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于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贬官,看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2] ”贬官的心态在这首诗中一览无余。当然不能说韩愈的文学成就都是在受贬后取得的,但他相当数量的佳文不受贬那是决然写不出的。
特别是《祭柳子厚文》,倘若没有相同的受贬经历,岂能相知如此之深?柳宗元也是一贬再贬,永州和柳州都是很不错的地方。可在当时,那可是瘴气和瘴病非常严重的地方。
在古人的心目中,只有中原才是可以居住的,其它地方均为未开化的蛮瘴之地,去那样的地方与送死并无两样,在这样的心态和交通颇为困难的条件下,没病也会紧张出病,这也加重了瘴气与瘴病说的可信度。这就是古代贬官所去之地今人大都觉得不错,而当时人都认为是一种极重处罚的原因所在。
无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贬,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只要翻阅柳文仍然会为其折腰。就是白居易不受贬也决然写不出《长恨歌》。
文字能够如此穿越时空,恐怕是受贬者自己也没想到的。至于苏东坡,那更是一位让人牵挂的贬官,“诗案”改变了苏东坡的生活,以至后人才有幸读到《赤壁赋》这一类千古佳作。
只是回头去看那些下手之人是何等忍心,今日读《宋史》可以看到李定等人如何从鸡蛋里找骨头,而下手最狠的应该算刘拯。刘拯,这个北宋的进士认为:“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扼腕。
愿正其罪,以示天下。”当时苏轼已给贬到了英州,而拯犹鸷视不惬也。
由此可见此人颇有点整人癖,最可笑的是这种有整人癖者还自诩为忠义之士。有这种癖好的人哪个时代都有,文革时期这类人表演得最为充分,就是今天这类人也远没绝迹,一些单位的无法和谐与这些人极有能量有关。
好在历史的法则总和这种人过不去,热衷整人者历史会将其淡忘得极快,后人谈论到贬官时会对此辈充满不屑,无论他们怎样工于心计又曾经怎样风光。贬官价值 不能说所有的贬官都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但却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
中国人爱把这些概括为“文能穷人”或是“文章憎命达”,这样的概括确有一定道理,但却会使人误以为那些整人者做下了天大的好事,把社会不公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实际上贬官的基数是很大的,而能够在遭贬后豁达澹定者毕竟是少数。
没人在意贬官者自己的感受,也很难真正理解贬官者的文字都揉进了自己的血和泪。诚如柳宗元在《牛赋》中比较了牛和羸驴、驽马的命运后所发出的感叹:“牛虽有功,于己何益!” 人才受贬会怎样伤害民族的筋骨?一次次对正直者的痛贬会怎样搞乱人们的价值观念?对社会风气会形成怎样的杀手作用?这是应该从贬官文化中吸取的教训。
如果总是满足于“愤怒出诗人”这一类理念,仍然只会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类虚话抚慰正直的受贬者,而使热衷吹牛拍马、玩弄权术、善于整人者如驴般活得滋润,那么即使有好文章问世,也只能说这样的社会是病态的。今天的文化发展早已走出了贬官文化的模式,这应该说是好事。
但贬官文化也启迪我们,寂寞是出成果的重要条件,大师们都是在大寂寞中修炼而成的。可今天连“小师”也耐不住寂寞,谁还能指望他们成长为大师。
过度的时尚与时髦可能会使原先文化大国的精神高度与一些蕞尔小国比肩。不知今天的文化人谁还能如贬官那样追问和思考?贬官们的文字或许有点灰暗?但在灰暗中显示了人性的深刻。
时下的文字颇为喧嚣,只是在喧嚣中显示了无法遮蔽的浮浅。古时贬官们的文字不动声色地在拷问着时下的文化,在爆炸式的文字增长中,有几许能够穿越时空?可以不再有贬官,但不能没有大师。
这是今天文化建设的两难,超越这样的两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什么时候文化人能够摆脱时髦这条疯狗的追咬,什么时候才可能出现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