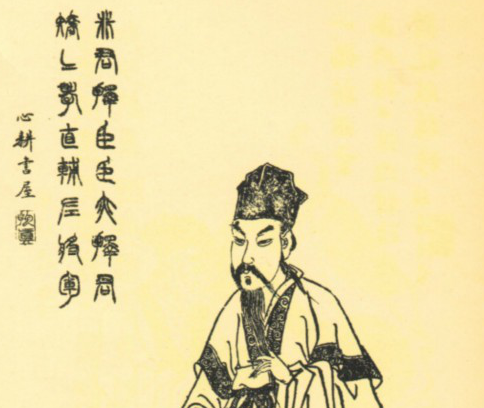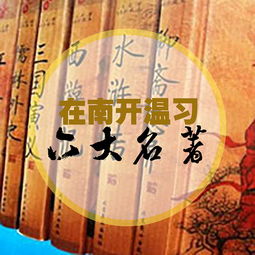
1.为什么《儒林外史》是"读书人命运的悲歌
《儒林外史》的思想境界
1. 揭露清朝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社会的腐败 我国清朝封建科举制度,使功名富贵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尺度,也是文人学士的唯一追求,极大的败坏了世态风俗人性。《儒林外史》从那些追求功名富贵、依附于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儒林众生及“名士”、劣绅身上领略到当时的社会病态与文化病态。
《儒林外史》以科场为轴心,深刻描写了儒林众生及“名士”、劣绅各类代表形象,从“病态人物”身上映衬出整个“病态社会”的基本面貌。
在《儒林外史》中,描绘的迂陋穷酸腐儒,都是受功名富贵毒害而不自觉的科举迷,是因为他们的愚昧、痴迷和随波逐流思想意识,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命运。 《儒林外史》的矛头不是指向他们自身的缺陷,而是指向那种对他们进行精神虐杀的科举制度。 《儒林外史》通过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的“丑与恶”的描绘,揭露侥幸者和骗取者在获得功名之后,对富贵的无耻无厌的追逐,体现了科场官场的黑暗腐朽。
作为官绅和市井棍徒,如果说娄三、娄四、杜慎卿等辈大多数只是或者只能在虚名假誉中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话,那些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多以营己利、谋权势为直接目的,因而更加卑鄙无耻,有时甚至穷凶极恶。
科举是求取功名的苦路,功名则是通向富贵的桥梁,少数举运者一旦成就功名,就要用无厌的贪求加倍地偿还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这些无耻官绅的培养基,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人民为之饱受灾难。 2. 乐道安贫淡泊名利,厌弃功名追求自由
《儒林外史》思想方面在否定性的批判后面,同时也透露出作者肯定性的追求。作者克服了理学的空疏与虚伪,表达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功名的厌弃。
《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其基本品质就是讲究“文行出处”,厌弃“功名富贵”。 “出”则德世济民,“处”则独善其身。而在腐恶的社会环境里,志士才人既不能施展抱负,“处”就成了他们洁身自好、乐道安贫的唯一对策。“处”实际上就是《儒林外史》正面形象的基本品质。
《儒林外史》中,开宗明义就写了一个王冕,他小时放牛为生,刻苦自学,得以精通学问,且成为名画家,但他不求官爵,卖画过活。县令具帕邀请,他坚辞不往;屈尊来拜,他也避而不见,甚至因此远走他乡。朱元璋慕名来访,他慨然晓以“仁义服人”之理,但朱称帝之后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闻风而逃,隐居会稽山中终不复出。他一生安于贫贱,不慕富贵显达,高风亮节,令人敬仰。作者以王冕故事做楔子,意在“借名流隐括全文”,犹如先立一面明镜,使书中那些接踵而至的“时文鬼”一个个在明镜中原形毕露。
《儒林外史》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而引发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近代民主观念,也一定程度上引导作者朦胧地趋向未来,向往未来的健康追求,自觉不自觉地使笔下的某些人物闪射出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
2.《儒林外史》第八回赏析
《儒林外史》第八回:(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赏析:
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出场开始是以仗义、爱结交有识之士的形象出现的,最后发现他们交友不慎、结交的人大多是没有什么水平的人,从而表现出他们自己水平也一般。
“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泯没了多少读书人的良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现实生活中,虽没有人因中了举人而疯疯癫癫,但却有人为了考取博士、硕士而不择手段;虽没有人仗着学识换来的权势蛮横乡里,但却有人卖弄自己的知识换取财富。周恩来曾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学习不该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祖国将来的繁荣富强。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以上供参考。
3.如何看待《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索
浅谈《儒林外史》对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启示在《儒林外史》一书中所描绘的大清王朝康雍乾盛世的背景下,作者刻画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或正面,或反面,把对于时弊的认识提高到了整个科举制度的认识,从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作为直接的抨击目标,充分揭露它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摧残,谴责它造成了势力虚伪的社会风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舍着性命去求功名”,只有科举才是求官的“正途”!功名富贵,核心在于做官,是封建知识分子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人的一个试金石,把他们放在这个聚光点上,足以显现其灵魂,使之纤毫毕露,声态并作地现身纸上。
《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体现了坐着对于知识分子社会出路和整体命运的观察和思考。所以这种批判必然导致对于所谓康乾盛世的全面否定。
从批判八股科举到否定功名富贵、抨击全社会的势利和虚伪;揭露八股流弊到揭露封建社会的种种弊政,所以《儒林外史》的全部描写都在告诉读者: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出路。一般的读书人,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很难做到像王冕那样,决意功名而又衣食不愁。
而反观我们当代社会,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怎么样才算是知识分子呢?那时的知识分子主要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一批文人。而现在不一样了,照《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说,像得到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亦或是科学家,也不一定算是知识分子。
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按照这一说法,似乎在中国当代也找不出几个知识分子,是非常苛刻的。而在海耶克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社会的背景,在康乾盛世,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束缚百姓的思想,控制他们的学术自由,采取各种政策,愚昧百姓,文人几乎没有任何出路。而我们现在的社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人民开化,思想开放,知识分子的出路更多了,能获得相对安稳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所以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加多样化了。
我们先看从政的道路,儒家思想是积极用世的,对于建功立名本身并不持否定态度,他反对的只是不讲文行出处的原则,寡廉鲜耻地去追求功名富贵。而《儒林外史》所讽刺的也只是口讲伦理,满肚子势利见识的假道学,对于真心恪守封建伦理规范的“真儒”则主要是肯定和赞美。
如范进从一个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变为科举制度的推崇者,中举前穷困潦倒,在科举制度的长期摧残之下,麻木空虚,中举后荣耀光彩,却连苏轼是何人都不知道,写出了当时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势利虚伪的社会风气。所以在我们现代社会,像“考公务员热”的温度持续不退,大家都想走向仕途。
其实追求功名也是非常正常的,是人都要食人间烟火,要生存也必须基本的经济条件。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去追求功名而不择手段,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要有骨气的,对于功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是最基本的,相对于一般人是更加高尚的,是追求节操的,所以不能因功名这些身外之物而丧失了自己的高贵的人格品性,知识分子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物质财富,既然身为知识分子,就不能过分被功名富贵所累。
我们再看学术研究的道路。传记中的王冕的形象被改造加工,写成了一个完全决意功名富贵,视功名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依旧维持着自己藐视权贵、孤高傲视的品格。
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吴敬梓也把这样的一个纯洁无暇、一尘不染的形象作为芸芸众生做人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专心搞学术研究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和政治搭上边,认真钻研自己学术问题,以免被功名坏了心境。
一旦研究学术成为一种功利性的目的,它就基本远离了学术的崇高性,反而沦为了庸俗。但是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不仅要凭借着自己的才华获取一定的政治地位,从而赢得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且他真正的使命不在于这些身外之物,而是传承和发扬。
正如吴敬梓写《儒林外史》,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中心,进而涉及教育、民生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晚期腐败道和没落的趋势。虽然最后宣传和实践“礼乐兵农”的政治主张以失败告终,但是有了这样的先驱者,前一个倒下,更有后来人奋起直追。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命脉,失去了命脉,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被打破,这个民族也就毁灭了。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人追名逐利,夺权夺势,能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可以说是已经没有了。
整个社会所弥漫的是虚伪造作的雾霾,整个社会体制也难以培养出这样精英式的人才。继2009年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以后,中国也找不出第二位这样的国学大师了,原因何在。